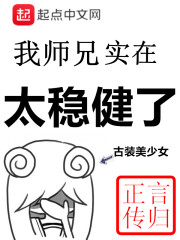求魔第三卷 名震東荒 第613章 短暫與美好(第四更)
容顏,看起來,是二十歲的摸樣。
這是虛假的,在其唯有十年的生命結束的那一刻,他會變成其本該具備的樣子。
蘇銘,離開了。
他為小丑兒的爹娘梳理了身堊體,使得他們的疾病散去,使得小丑兒臉上那胎記更淺之後,他沒有去推開屋舍的門,而是邁步間,出現在了屋舍外。
「如果沒有推開那道離別的門,便等於是我沒有離去的話,那麼我永遠不會去推開這個門。」蘇銘的身後,是無盡的雪花,那雪花遮蓋了他與小丑兒一家屋舍的道路,似斷了歸途,漸漸成為了一片白色的蒼茫。
蘇銘獨自一個人,孤獨的走在雪地上,越走越遠,那雪花落在他的頭髮上,身堊體上,還有那件棉襖上……很冷,可他的心中埋着那溫暖,在這雪中,可以溫暖着他,讓他走的更遠。
蘇銘遠去了,走在這天地的白雪裏,直至一個人孤獨的走到了白頭,那消失在天地的身影,在蕭瑟中,漸漸看不清,漸漸化作了雪….…
那雪風的嗚咽,如一首塤曲的飄遙,那雪花的飄落,則是這塤曲的歌詞,在這虛無里唱着,不知誰能聽到的歌聲。
那歌聲里,唱着風雪埋葬一座城,唱着孤獨散滅所有的燈,唱的是看不到的陌生中,誰的夕陽,誰的容顏,誰的兒時十幾年……
在蘇銘離去後,小丑兒一家中,在這沉睡里,那躺在床堊上的陳大喜,慢慢的睜開了眼,他的目中有一抹迷茫,他覺得自己睡了一覺,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。
那夢裏的最後,有一個聲音迴蕩,正是這聲音,將他從夢裏帶了出來,帶回了家。
「你本是死亡之人……我能做的,是幫你爭取十年的生命,用這十年……去陪伴你的爹娘,你的妹妹……」
我不知道這一章是怎麼寫完的,寫着寫着,忽然有種迴光返照的感覺,實在沒有其他的詞語來形容,姑且這麼形容吧。
感覺一下子充滿了力量,可寫着寫着,就整個人更深的疲憊下來,回首這一個月,唯有一個字。
與累無關,我不說…
第三卷 名震東荒 第613章 短暫與美好(第四更)